香港淨移出人口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廖亮羽寫的 風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自由時代 和舒國治的 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秀威資訊 和廣西師範大學所出版 。
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陳明通所指導 魏淑娟的 香港民主的基礎~從香港民眾對立法會存廢態度分析 (2020),提出香港淨移出人口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一國兩制、立法會、民主、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而第二篇論文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夏林清所指導 張貴英的 位移的抵抗性政略之生成-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構形 (2011),提出因為有 移住性工作者、人口販運、流動、跨國移動、抵抗性策略、性/別底層、女性生命、生存脈絡的重點而找出了 香港淨移出人口的解答。
風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自由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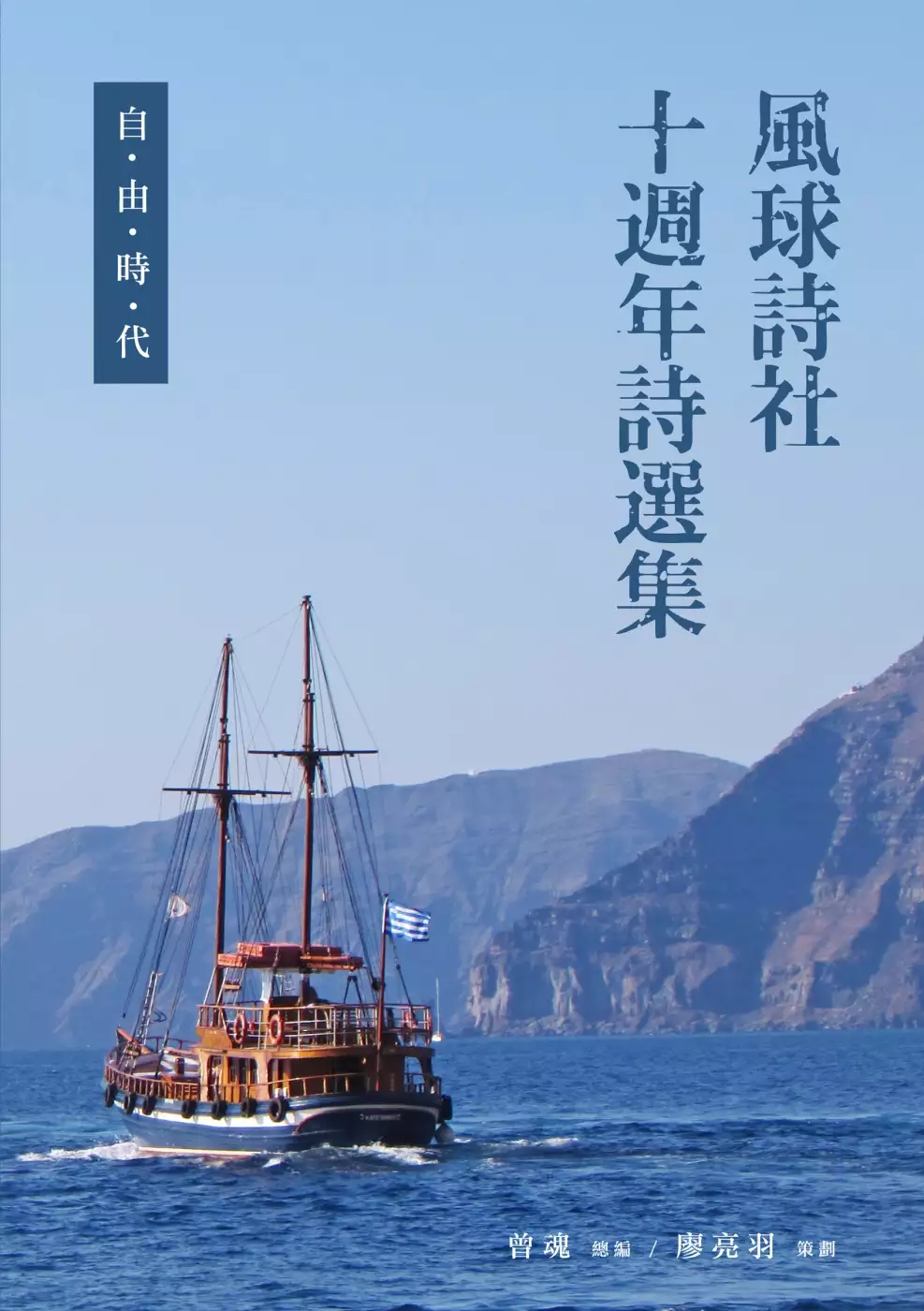
為了解決香港淨移出人口 的問題,作者廖亮羽 這樣論述:
漫漫十年,自由時代早已展開,一個詩社的熱帶氣旋訊號,宣告仍然生效。風球詩社十週年詩選集輯錄北、中、南和東部社員,合共一百二十首作品,涵融不同主題和風格之創造,無有標幟特定的美學典範。 如詩人瘂弦所言:「不管你寫什麼,點的或面的,局部的或全體的,個人的或民族的,只要寫得好,都有社會意義。」這也許正是風球詩社的社會意義,推行著面貌多元的書寫、讀詩會、詩展、文藝營,甚或跨領域藝術結合的試驗。願風球持續懸掛,那股柔和卻勢猛的力量,尚且旋轉迴環。與詩素昧平生的人,與孤獨的詩人,我們或終將在風中謀面。 本書特色 ★風球詩社集合了眾多十六、七歲到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牢牢
掌握住詩之純粹力。 ★他/她們是一群把詩當作人與人之間的潤滑劑和感情的黏著劑在生活的愛詩人。 ★這本詩選不過是他/她們偶然興起留下的一本遊俠手冊而已。當這些網路遊俠向更熟成的青壯年邁進時,當今詩壇的眾將官們、守城人等,可都要當心了! 名人推薦 |詩壇名家.專序推薦| 白靈(詩人、台北科技大學及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 楊宗翰(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陳政彥(嘉義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本詩社詩選的出版豈是易事?風球以「自由時代」標稱此選集,說明了台灣是處在言論自由、行動自由的年代,在詩的書寫領域裡是絕對的百無禁忌。」──詩人 白靈 「因為校園詩社無論再怎麼
跨校,畢竟多屬情感集合體,是友誼團、舒適圈兼青春園。而強者在創作上是不必圍爐取暖的──因為他們自己就能生火,自己便在發光。」──教授 楊宗翰 「除了能讀到個人詩藝的光彩,也清楚看到台灣詩壇的未來。風球正默默捏塑未來台灣現代詩的臉龐,相信此一難得的努力將會給未來台灣現代詩帶來一副亮麗的模樣。」──教授 陳政彥
香港民主的基礎~從香港民眾對立法會存廢態度分析
為了解決香港淨移出人口 的問題,作者魏淑娟 這樣論述:
港英政府管治末期,雖為香港引入代議民主制度,並以《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建構「高度自治」的行政體制,惟「一國兩制」的主導權仍牢牢掌握在北京手中。2003年「七一」超過50萬港人走上街頭的抗爭行動,強大的反政府力量令北京中央政府震驚,並重新評估與調整對港政策,嗣後北京介入香港事務漸深,壓制異見的手法也更加強硬。為防止泛民主派透過參選影響議事及抗衡行政體制,北京除高度介入選舉,並以人大釋法否決及推延特首及立法會普選的政改方案,更首次就香港事務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主張擁有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儘管如此,香港民主意識仍持續高漲,政治運動更轉趨激化,面對北京全面介入及管控香港事務,香港的民主基
礎是否因此動搖,未來香港是否仍能保有民主元素繼續實施民主制度,為本論文的研究課題。鑑於立法會為香港民意機構,本論文依據臺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香港調查研究計畫」2012年及2016年的兩波調查統計資料,進行「香港居民對立法會存廢態度」分析,並透過立法會歷史沿革及民主運動之梳理,以及2016年迄2021年相關文獻與歷史事件對照分析,推論影響香港民主的元素及香港民主化的變遷與發展。本研究發現,人口學變數與立法會存廢態度具關聯性,其中70歲以上受訪者呈現更為贊成廢除立法會及選舉之態度,顯示長年關注及投入香港民主改革之民運耆老為影響香港民主之重要元素。另社會學變數中以天主教信仰者
及中產階層呈現更為贊成廢除立法會及選舉之態度。本研究推論,由於多位香港政界知名人士是天主教徒,使同為天主教徒之香港民眾對守護民主價值有更多的同理與支持;而香港青年公民等中產階層,在2003年「七一」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及2019年「反送中」等民主運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亦為影響香港民主之重要元素。此外,在政治學變數中,對立法會信任度、自主權及制衡權等變數,均與立法會存廢態度具顯著關聯。「雨傘運動」後,北京透過宣誓效忠等政治審查,撤銷多位議員資格;「反送中」運動後,北京繞過港府制定《香港國安法》,清洗異議人士,並通過修改香港選制建立「愛國者治港」體系,阻絕民主派人士參選,削弱工商界對港
府施政之干擾,行政長官的自主權亦遭剝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多位民運耆老身陷囹圄,中產階層紛紛移居海外,泛民主派的力量分崩離析。新選制下反對黨參選及影響政局的機會渺茫,立法會在無制衡力量下,已淪為橡皮圖章,而國際智庫民主指標亦顯示香港民主元素正加速消逝中。
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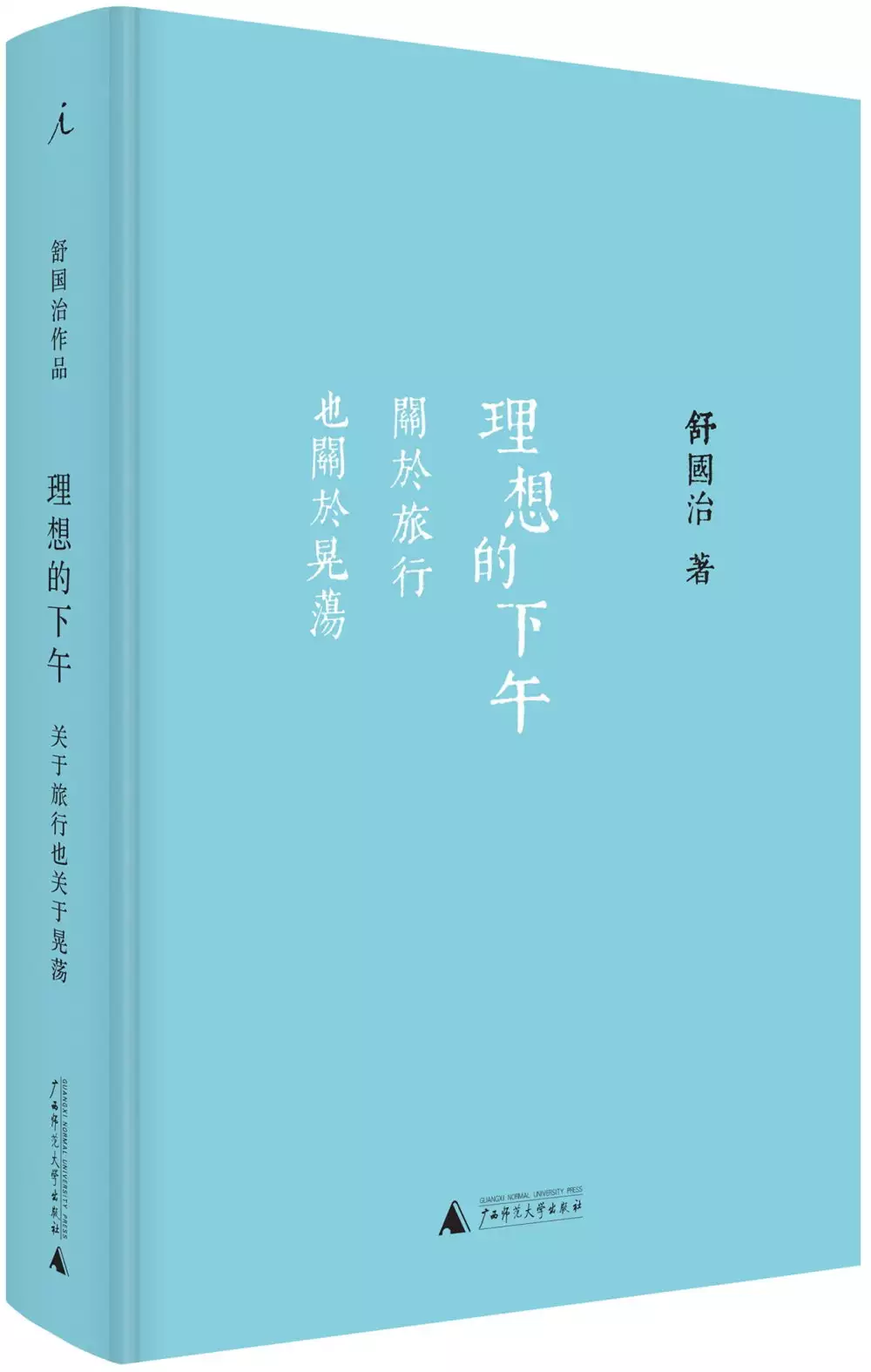
為了解決香港淨移出人口 的問題,作者舒國治 這樣論述:
梁文道長文推薦 風靡無數文藝遊子的行囊必備之書 迄今為止,最有態度的旅行文學佳作 關乎旅行,也關乎晃蕩,更關乎生活。 信步由之,放眼而望,清風明月時時得於道途,卻無須擁有也。 本書以一種超俗的眼光,與閒散的人生情懷,講旅行、講山水,看待周遭、尋覓佳境。自十年前在臺灣出版後,風靡了無數文藝遊子,幾乎人手一冊。簡體版較之繁體版,篇幅擴大增加,喜好旅行文學者,不可錯過。 舒國治的散文原就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正由於其古老,他才能迷倒一眾臺灣讀者,成為彼岸十年來極受歡迎的散文家。 我見過詩人很不“像”他的詩,更常見到小說家不“像”他的小說,卻從未見過有散文家不像他的散文的。所以張中行就像張中
行,餘秋雨就像余秋雨,龍應台就像龍應台;舒國治,他的人就走在他自己的文字裡,閒散淡泊,品味獨具。 ——梁文道 舒國治,一九五二年生於臺北。原籍浙江。是六十年代在西洋電影與搖滾樂薰陶下成長的半城半鄉少年。七十年代初,原習電影,後注心思于文學,曾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備受文壇矚目。一九八三至一九九〇,七年浪跡美國,此後所寫,多及旅行,自謂是少年貪玩、叛逆的不加壓抑之延伸。 而文體自成一格,文白相間,簡淡中深富雅韻,論者鹹認與他的清簡度日有關。常人忽略的清苦生活之美,最受他無盡窺探與詠頌。著有《理想的下午》《流浪集》《門外漢的京都》《臺北小吃劄記》《窮中談吃》等。
序 但少閒人/梁文道 哪裡你最喜歡 城市的氣氛 冷冷幽景,寂寂魂靈——瑞典聞見記 早上五點 旅途中的女人 外地人的天堂——紐約 托友人代訂車等旅遊事 理想的下午 推理讀者的牛津一瞥 早春塗鴉 老旅行家永遠在路上 漫無根由的旅行者 旅行指南的寫法 再談旅行指南 一千字的永康街指南 賴床 散漫的旅行 紐約登峰造極小史 舟車所至 割絕不掉的惡習——逛舊書店 旅夜書懷 歲月沒有使她老 在旅館 旅館與臺灣人的起居 如何經營民宿 十全老人 喪家之犬 咖啡館 在途中 臺灣最遠的咖啡館 咖啡館的掌櫃 我是如何步入旅行或寫作什麼的 “若選擇住,我不會選紐約。……最主要
的是它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歡它,便因它抽象;這是紐約了得之處,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這點。而我,還沒學會喜歡抽象。” “日本是氣氛之國,無怪世界各國的人皆不能不驚迷於它。” “英國的全境,只得蕭簡一字。而古往今來英國人無不以之為美,以之為德;安于其中,樂在其中。” 除了舒國治,我想不出還有誰能簡簡單單地只用兩個字就這麼精准地寫出紐約的抽象、日本的氣氛,以及英國的蕭簡。早在十四年前,我就領教過他這過人的本事了。那年香港快要回歸,他正預備要寫一本談香港的書(但始終沒有完成),於是我請他到我家裡夜聊,向我這個土生港人形容一下他所知道的香港。沒想到他竟然把這片我們傳統上習稱為“福地”的城市形容
為“窮山惡水”。“由於沒有多少平地,他們總要在那麼彎曲狹窄的水道旁邊蓋樓,這些樓一面緊貼被人工鏟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折的海岸了,這麼險要的形勢,竟然就住了這麼多人。”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很對,從這個角度看來,香港的確很像一座擁擠的邊塞,住滿了無路可逃的難民,此處已是天涯海角,再往前走就是陸秀夫負主投海的怒洋了。這,如何不是“窮山惡水”? 舒國治眼光銳利,甚至可以說是毒,否則又怎能如此獨到又如此準確地掌握一個地方的特質呢?可是你千萬別以為他是那種禿頂冷沉、漠觀世情的思想家,不,他高高瘦瘦,走起路來像風一般迅捷,十分清爽,而且常帶笑容,隨處安然。他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檔的餐館裡暢飲貴價葡萄酒,
但他自己的生活在許多都市人看來卻遠遠說不上舒適。住在溽熱的臺北,他竟然堅持不裝冷氣,家裡也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例如電視。就像他在《十全老人》裡所說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於瓦頂泥牆房舍中,一樓二樓不礙,不乘電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顧盼縱目”,“穿衣惟布。夏著單衫,冬則棉袍。……件數稀少,常換常滌,不惟夠用,亦便貯放,不占家中箱櫃,正令居室空淨,心不寄事也”。基於同樣的原則,“聽戲曲或音樂,多在現場。且遠久一赴,不需令餘音縈繞耳際,久系心胸。家中未必備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備書籍同義,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 “家徒四壁”,這是何等的好品味,何等的好生活?今天老把“奢華”“尊貴”掛在嘴邊之輩
,恐怕還要再過十多年才能領略其中意趣。 我不想說太多舒國治這個人的事,我想談的其實是他的文章。只是他的為人為文無法不讓我想起“文如其人”這句老話,所以言其文就不得不從他的行止風範談起了。可是,經過現代文學理論的洗禮,人人皆知作者已死,“文如其人”早就是老掉牙的過時神話了,為什麼我還要用它去概括一位作家的書寫呢?那是因為舒國治的散文原就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你看,許多年輕讀者不都說“舒哥的作品不像是現代人寫的”嗎?正由於其古老,他才能迷倒一眾臺灣讀者,成為彼岸十年來最最受歡迎的散文家。 舒國治的古老,或許在他行文的韻律節奏,也在他用字的選擇,比如:“波羅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島嶼,將斯德哥爾摩附近的
水面全勻擺得波平如鏡,如同無限延伸的大湖,大多時候,津浦無人,桅檣參差,雲接寒野,澹煙微茫,間有一陣啼鴉。島上的村落,霜濃路滑,偶見稀疏的Volvo車燈蜿蜒遊過。” 然而,正如“V01vo”這個洋文所提示的,舒國治究竟是位受過洋化教育、見過世面的現代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趁著心裡頭仍抱一股嬉皮餘風,獨自浪遊美國,按圖索驥,從一個小鎮走到另一個小鎮,每至一處便打點零工,攢點小錢,住得差不多了便再收拾行囊上路。此前,他本是臺灣文壇的新星,以一篇小說《村人遇難記》贏得無數前輩驚異。而他居然放棄了自己的“前途”,忽然從大家的目光中徹底消失。 等他回來,舒國治已經漸漸變成另一個人了。雖然他偶爾還會寫
下這樣的句子:“她微低著頭,眼睛視線不經意地調在前下方的地面,輕閉著唇,有時甚而把眼皮也合上一陣子,隨著車行的顛簸,身軀也時而稍顯移晃。”“文藝”得很像當年那位深具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家。他甚至不忌“破壞性”和其他各種這個“性”那個“性”的西化造詞。但是,大家卻發現整體而言,從美國回來之後的舒國治竟然變得更古老,也更中國。 因為他居然以散文為業,而且是一種很不時髦的散文。 散文原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遺忘的地步(難怪我曾見過有些年輕人會批評某某某不寫小說不寫詩,所以不算作家。可見在他們看來,就連周作人、林語堂和梁實秋的作家地位也變得很可疑了)。當然,散文還是存在的,就文體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見最
普及的,小至一條手機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歸入廣義散文的範疇。正因其常見普及,散文遂成了一種最不“文學”也(看起來)最不必經營的文類。比起詩、小說與戲劇,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飲水,凡常而瑣碎。 我猜測這便是今日大陸雜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們的期待裡頭,雜文應該寫得機巧銳智,處處鋒芒;它的經營痕跡是鮮明可見的,它給讀者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緊的,是它往往夾帶議論;所謂“有思想”,所謂“以小觀大”,皆與雜文的議論功能有關。相比之下,傳統散文未免顯得太過平淡,花草蟲魚之屬的內容也未免太沒深度。於是“美文”就興起了,仿佛不經一輪斧鑿,一番濃辭豔飾的堆砌,散文的“文學性”就
顯不出來。於是“文化大散文”就抬頭了,似乎不發一聲文明千年的哀歎,不懷國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夠“深刻”。這麼重的口味就好比現時流行全國的川菜(尤其是那些劣品),吃得太多,你就再也嘗不出一口碧綠小黃瓜的鮮脆真味了;見到一尾活生生的黃魚,你也只能想像它鋪滿紅料躺在炙火上的模樣。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舒國治的散文古老。你看他有多無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寫賴床,而且還要討論賴床怎樣才算賴得好:“要賴床賴得好,常在於賴任何事賴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過日子,過一天就要像長長足足地過它一天,而不是過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後他還能分辨一個人是不是賴床的人,因為“早年的賴床,亦可能凝熔為後
日的深情。哪怕這深情未必見恤於良人、得識于世道”。“端詳有的臉,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長時沒賴床了。也有的臉,像是一輩子不曾賴過床。賴過床的臉,比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態,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遙想,卻又不甚費力的那種遙想。”也許是我見識不廣,但我的確好久沒見過有人這麼認真地去寫“賴床”這樣的題目了,如斯細碎,如斯的無有意義。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沒有埋伏一句引人驚歎叫人發噓的punch line;也不聯繫什麼名人偉業,沒有扯出什麼賴床賴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實實地寫賴床:“我沒裝電話時,賴床賴得多些。父母在時,賴得可能更多。故為人父母者,應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賴床。” 舒國治的散文更不是一般意義
的“美文”,儘管它的確與“審美”(aesthetics)有關。這種審美是某種感官能力的開啟,常如靈光一閃,以清簡的文字短暫地照亮俗常世界之一隅,就像《哈利·波特》裡面那“國王十字車站”裡多出來的一個月臺,一般人是看不見的,惟待魔法師隨手一揮,它才赫然敞現。可是那座月臺卻示現得穩穩當當、平平無奇,仿佛早已在此,良久良久;而你之前明明看不到它,等到見著了,竟也不太訝異,覺得一切盡皆合理、凡事本當如是,只是自己一時大意,過去才會對它視而不見。 這便是專屬散文的獨特美學了,不像詩,它不會劇烈扭轉觀看事物的角度,使得宇宙萬象變得既陌生又奇兀;相反的,散文總是稀鬆平常,就算說出了點你想都沒想過的道理,你
也忍不住要點頭認同,“是啊,事情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似乎你很久以前也曾想到過這一點,只是不知怎的卻把它給忘了。 就拿蘇軾那篇膾炙人口的《記承天寺夜遊》來說吧,全文不過百字,你說它講了什麼大道理呢?沒有。你看它的修辭用字很華麗嗎?也不。但大家硬是覺得它美,硬是要把它看成中國小品文的精萃。為什麼?因為它好像說了很多,實際上卻又什麼都沒說過。正是“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月夜竹柏有誰沒見過呢?問題只在於“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所以散文的審美與散文家的想像力是與眾不同的,他用不著像詩人那樣祈靈繆思,好在眉心修煉出一隻魔眼;也用不著如小說家那般閉戶向壁,苦築一座不存在的蜃樓。他只需要閑下來一些,便見
“庭下如積水空明”;然後再閑一些,便能將這很多人也許都曾看過但又不復記憶的景象寫下來。他不該太費力氣,也不可太著痕跡,輕輕一拭,那蒙灰的鏡片方能頓時明朗,令人感到眼前萬事依舊,可自己就是比往常看多了些什麼。 出入塵世而不滯著,故閒人如舒國治者才能道出樹木與房合的本來面目:“再怎麼壁壘雄奇的古城,也需有扶疏掩映的街樹,以柔緩人的眼界,以漸次遮藏它枝葉後的另一股軒昂器宇,予人那份‘不盡’之感。”在這種目光的觀照底下,就連下午的陣雨也意外的可喜:“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陣雨,霎時雷電交加,雨點傾落,人竟然措手不及,不知所是。然理想的陣雨,要有理想的遮棚,可在其下避上一陣。最好是茶棚,趁機喝碗熱茶,
驅一驅浮汗,抹一抹鼻尖浮油。……俄頃雨停,一洗天青,人從簷下走出,何其美好的感覺。”而你卻不覺這是故作怪論,強替陣雨說好話,反倒勾起了你記憶中的經歷,去其狼狽,存其真趣,自己在心裡細細印證他這番話的味道。 由於散文這種獨特的審美面向太過貼近現實,不是這種心境,不是這種性情,便很難真切地寫出這種稍稍偏移出現實的現實,所以“文如其人”的古訓最能適用在散文家身上。我見過詩人很不“像”他的詩,更常見到小說家不“像”他的小說,卻從未見過有散文家不像他的散文的。所以張中行就像張中行,餘秋雨就像余秋雨,龍應台就像龍應台;舒國治,他的人就走在他自己的文字裡,閒散淡泊,品味獨具。我知道有些大陸讀者看到這裡就已
經忍不住要說“這種品味很小資”了,他大概看了太多流行時下的廣告,也大概太過年輕,遂將態度的悠閒與生活的講究生硬地等同於“小資”,乃至於忘記了中國散文的古老傳統,忽視了消費喬裝以外的做人美學。 上一回在北京見到舒國治,我問他接下來會去哪裡玩,不料他答道:“河南陳家溝。”我沒聽過有人會去那裡旅遊,非常好奇,接著他便解釋:“陳家溝是陳氏太極的發源地,我想去看看。”我知道他不打拳,也不迷武術,他真正的理由可能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不用再問,我就曉得他一定會先坐硬臥火車,聽人家夜裡喝茶聊天嗑瓜子;再乘大巴,隔窗觀看道旁推車的老漢;眼皮稍倦,就合上小睡一會兒。等到一覺醒來,說不定便是陳家溝了。至於他回
來之後會不會寫篇文章記記那裡的風土人情昵?也許會,也許不會,但這又有什麼要緊的呢。
位移的抵抗性政略之生成-移住性工作者的生命構形
為了解決香港淨移出人口 的問題,作者張貴英 這樣論述:
自古以來,人們的跨國流動就不斷地在形塑著國家與社會的界線,近年來流動以擴展到全球性的範圍.成為國內與國際政策的焦點.這些流動對經濟與社會產生大規模及長遠的影響.經濟移動中一股重要的族群就是性工作者,無論是以觀光.短期工作簽證的合法管道獲是採取偷渡.(假)結婚等方式進入他國從事性工作,都是當代社會非常重要與複雜的課題.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探討11未來自歐美與亞洲等各國的移住性工作者之生命脈絡,以及當前人口販運防制法與國家邊界控管政策的謬誤,藉以檢視深層的生命動能,彰顯其抵制性政略的生成歷程,並理解各項國家政策及全球政經生態對其共構互動之影響.研究者透過探索移住性工作者生命與勞動的經驗理解,希冀開
展出自我行動的抵抗性知識方法.本論文探究中,抵抗性知識方法形成於研究者與性工作者.母親和單親社會福利工作中的底層家庭,在全球化移動下的生命搏鬥.生產知識,並且相互陪伴前行的歷程之中.研究發現遷移賣春求生.不等於人口販賣.移住性工作者(Migrant sex worker)是全球化之下的移民拓荒者,而非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她們跨界移出.移入從事性工作謀生,翻轉自己與家人的命運,卻因為移動與性工作的污名而面臨多重困境.本研就建議:應重視移住性工作者的個別生命動能,及其累積之細膩抵抗性政略,藉以省思並檢視社會結構壓迫處境對移動脈絡之影響.